①诅咒
我在星球的表面飞行。在一片广袤而无趣的沙漠之上,残破的古董向着远处斑驳的灯光飘去。绿意如星光倏忽消逝,沙尘勾勒出风的形状。天空在变亮——比我所熟知的夜空多了无数色彩。城市就在前方。
而在此之前,我甚至不知道原来这里也会有城市。我以为这颗星球只有荒漠,荒漠,无尽的荒漠。我曾以为,这块被人们称为“荒原”的土地,会是我生活的全部。
但当防空警报拉响时,我意识到,也许荒原真的会成为我生命的全部。
即便我不属于荒原。
即便我们卡塔斯多夫家祖祖辈辈,都是荒原的外来者。
幸好,还有点时间来回忆我们的故事。
②荒原与卡塔斯多夫
我讨厌这片土地。
我想逃出去,却又不知道自己的故乡是在何方。
从出生开始,我的世界就局限在这颗小小的荒漠星球上。漫无边际的黄沙灌满所有的视线,视线越过起伏不定的沙丘,你能隐隐看到远处挣扎的点点绿色,还有指向远方的半掩骸骨。稍微稳定的地带是沙鼠们的天堂,是全副武装的大人才能去的猎场。只有每周定时飞来的运输飞船寄托着我对外界的想象。而除此之外,是死寂的荒原。
运输机飞来,抛下装着底限物资的大铁皮箱,又吊走上一个。它们的工作高效、精准,每周六我能看到它们的时长永远不会多一秒或者少一秒。没有人会想混进铁皮箱里被带走——没人能忍受零下百度的低温。
再说了,荒原里的人都是战争的难民,本就是逃来的。“联盟”和“帝国”间的战争反反复复,散布苦难。而比起战争,他们更讨厌的就是卡塔斯多夫家的人。从我的曾祖父阿卡夏·卡塔斯多夫开始,就一直如此。
人们把我们在地面上的房子叫“女巫堡”,因为它就像久远传说中恶毒女巫住的矮堡。可是它既没有尖顶,又只有两层。如果说真有什么神奇的地方,那就是它足够结实,再大的沙尘暴也吹不倒。荒原没有这种结实的材料,这里只有沙土,甚至连洞屋都需要挖在几米深土质稍微结实点的地下。这让我对建造女巫堡的曾祖父充满了崇敬。
曾祖母伊迪悄悄告诉我,女巫堡是曾祖父从老屋拆下的材料盖的。老屋坐落在数公里外的一片琉璃地里,我从没去过。有时我想,曾祖父是如何从老屋一点点拆下那些闪着奇异光彩的合金,在狂暴的风沙中一点点盖起了女巫堡。
不过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和荒原人一样,学啮齿动物住在地洞里。每天晚上,我就伴着伊迪的故事入睡。但我已经离伊迪而去,尽管时间不多,我也得学着自己讲故事了。
③曾祖父
我想要逃出荒原。和我的哥哥,路易·卡塔斯多夫一起,逃出这片不愿意接纳我们的土地。
我的哥哥路易是个行动派,小小的地洞装不下他的求知欲。
“烦!”有一次他在我面前抱怨,发疯一样地挠着头发。“莫里安,你就不想去见见新东西吗?”
在一开始,他只是想偷偷溜去老屋看看,因为那是健谈的老伊迪唯一不愿多说的地方。一到晚上,我让伊迪来我房间讲故事,他就趁机跑出去,在伊迪回去女巫堡之前又溜回来——在伊迪锁门之前。
伊迪每晚都会来讲故事;故事讲完了,她会趁机给我讲起卡塔斯多夫家的往事。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
“50多年前,你曾祖父阿卡夏和家里闹了矛盾,带着我和两个儿子来到了荒原上——”
那时,荒原人对卡塔斯多夫家还怀有善意,以为又是哪儿来的新难民,毕竟联盟和帝国的战争还在继续。厄舍尔家的小儿子,也就是我的外祖父,还邀请曾祖父去参加荒原的大选。大选推举出来的领袖负责分配每周投下的物资,是个责任重大的职位。投票的时候,每一户人家都要在心仪的候选人面前的沙地上丢只死沙鼠,作为自己的选票。
伊迪不无自豪地说,当时曾祖父面前还有不少沙鼠呢!不过曾祖父没有当选。伊迪觉得是因为他面相太凶了。曾祖父是个极严肃又不苟言笑的人,他喜欢动手胜过言说。他曾一声不响地驱走了来帮忙挖地洞的人,然后自己一点点盖起了地上的女巫堡。他不喜欢笑,他高兴时身子会有节律地上下耸动,“好像谁在他耳边播着蓝调。”
曾祖父的家教也很严格。他让我祖父和他的弟弟多比在成年前不许和荒原的人接触。要是被他发现和荒原的小孩混在一起,曾祖父的两撇胡子就会夸张地竖起来。听话的祖父和安静的植物打交道去了,可是弟弟多比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到晚上,精力无限的多比从女巫堡的窗户跳出去,和他们的朋友们尽情欢闹。
多比是个天生的喜剧演员,总能把所有人逗得前仰后翻,那顶旧礼帽和他的小身子尤其相称。“多比是只小鸟,总是要蹦蹦跳跳飞出窗的。”伊迪讲起他的时候,看向床边的油灯,表情柔和得好像多比就在火焰中对着他微笑。我不禁想起花园里的墓碑,其中一块刻着一个长着翅膀的微笑男孩,下边写着:
“多比·卡塔斯多夫,A.D.2110——2123”
"那他是怎么死掉的呢?"我瞪大了眼睛问。
但伊迪像是没听见一样,木偶般地呆坐着。就在我正要再重复时,伊迪浑身一哆嗦,目光从灯焰移回我的脸颊,然后长叹。
“是了,莫里安也长大了。”她从怀里掏出一个白色的无字药瓶,抖出几粒粉色的药丸,以一种不紧不慢的优雅姿态就水服下。这么做之后,她的眼睛似乎都清明了几分。
多比几乎是摔死的。
他偷偷带着伙伴们去了那片琉璃地。他从老屋的顶上摔下来,头冲着光滑的地面。摔下的高度并不高,他只是严重的脑震荡。他的“伙伴”们看着他摔在地上,一会儿爬起又滑倒,滑倒又爬起,一开始的惊恐竟逐渐散去。大家指着多比笑起来,以为这又是什么新的表演剧目。多比最后抬起头来,歪歪斜斜地迈步,继而又最后一次滑倒,头装在一根突出的锥刺上。他的旧礼帽落在一边。随着身体的抽动,却没有那句他最爱的“先生们女士们,表演结束了!”。
那是一个如今晚一样晴朗的夜空。从头颅流下的血液亮莹莹的,似乎混杂着什么白花花的东西。荒原的孩子们被吓到了,他们中最胆大的一个跑去了女巫堡报信。被问起的时候,他们谁也不知道多比为什么爬到老屋上,又从上面摔下来。曾祖父亲手埋葬了自己的小儿子,好几个星期沉默不语。
那是卡塔斯多夫家刚来到荒原不到半年的事情。
多比的死似乎打开了某种厄运的开关。运输机继续送来物资,接连好几次后,荒原人终于确信食物和水并没有增加应有的量。也就是说,卡塔斯多夫家并不是登记过的难民——而他们要与这些真正的难民抢食吃了。
板着一张脸的曾祖父被手持各种工具的荒原人团团围住,尖锥、铁锹。厄舍尔家的小儿子,当时的领袖问他:“你们没有去登记? 没有登记的难民,来不了这个收容区。”
曾祖父没有回答这个年轻人的问题。他说:“卡塔斯多夫家可以少分点。我们带有种子,可以种地。”
“不可能!荒原什么也种不了——”
人们开始吵嚷,开始颤抖。他们早就不爽这家人了,不论是那座女巫堡,还是他们举手投足的上层气息,都让他们心生厌恶。
恶意如潮涌。曾祖父束手无策。
“他最后怎么做的呢?”我问。
伊迪咂咂干瘪的嘴唇,“他们只能匀出两个人的物资。”她缓缓地说,“只有我和你祖父留了下来。”
我想起来曾祖父的墓碑上,画着一把生花的手枪。
“你该睡觉了,小莫里安。希望你不会做噩梦。”
“我不会的,伊迪——明天我还要听你讲!”
伊迪离开后没几分钟,路易哥哥就冲进了我的房间,一脸兴奋地把我摇醒。
“莫里安!是飞船啊,飞船!”他低吼。
“那个老屋,那不是什么旧房子——”
“那是艘飞船!星际飞船啊!”
他的表情宛如一个毒瘾初解的瘾君子。
“说不定很快,很快,我们就能离开荒原……”
④祖父和凯蒂姑妈
计划便实施了。
每天晚上,我继续缠着伊迪,而路易哥哥继续溜进老屋——那个破败的飞船里,寻找离开的办法。在每一个寂静的长夜里,我都同时接受着宛如两个世界般的两个故事:
伊迪说,曾祖父死后,祖父很快和一个荒原女人结婚了,育有我父亲和姑妈凯蒂。不知为何,卡塔斯多夫家一直没有去难民登记。祖父一直致力于在荒原种出粮食来,以缓轻几分生活的压力。他常常一言不发地去老屋鼓捣什么,又阴晴不定地走出来。
路易说,老屋的数据库里写着卡塔斯多夫家是逃离战乱来的上流家庭。在卡塔斯多夫的故乡,被称为“帝国”的地方,人人的基因都接受过改造,使他们随时能成为战场上勇猛的士兵。但同时,如果没有某种特殊的药物辅助,被改造过的人类更容易患上各种精神疾病,在疯癫和理智的夹缝中度日。卡塔斯多夫家也不例外。这确实不假,他自己的狂热表情就是最好的印证。而他自己提出的论据,则是祖父在老屋一台巨大机器上的操作记录:
“基因定向诱变程序,已操作5612次,已剪切17088次,误操作发生134次,10个样本已保留。”
为了这个数据,祖父花了十年。卡塔斯多夫家的人,都是些偏执的疯子。
伊迪说,祖父最后成功了。他带回来几袋种子,它们都能在荒原成长,结出营养丰富的果实。而随着生机勃勃的藤条一起长出来的,还有祖父身上134次误操作积累下来的异变。随着饮水,祖父的身上开始长出绿叶,抽出新芽。皮肤开始发暗,脚趾开始伸长变形……
简单地说,祖父慢慢变成了一棵树。一棵矗立在女巫堡旁,树荫能盖过整个矮堡的大树。
祖父没能活过第二个旱季。他的躯干变成了木材,根系成了花园地基,枝叶花果散入了荒原各家各户,他的墓碑上则刻着一片叶子。而他带回来的那些奇异的作物,则被善良的伊迪分给了荒原各户。
在祖父的旁边,埋葬着我的父亲和姑妈。父亲是个开朗豪爽的人,他娶了厄舍尔家的大女儿,海伦·厄舍尔,我的母亲,然后半入赘一般地住在厄舍尔家,几乎再没回过女巫堡,似乎在远远的躲避着什么。
至于我的姑妈,凯蒂,好像从来没有受祖父离世的影响,不像我父亲几乎是逃狱一般地逃出了女巫堡。凯蒂姑妈一直呆在女巫堡,性子古怪刁蛮得很,即便脾气好如伊迪,也常气得指着她骂“不识好歹”之类的话。
“那我也是你孙女,”凯蒂姑妈会高高挑起下巴,以一种高傲的姿态躺在祖父的摇椅上,“我也姓卡塔斯多夫,您还能赶我出去不成?”
姑妈早早结了婚。我的姑父是那种看起来白净高瘦的小男人,和姑妈站在一起颇有一种富婆与小白脸的既视感。他说他是个作家——至少梦想是当个作家,入赘卡塔斯多夫家就是为了取材。
这个小家庭最终也破碎了。硬要说的话,我猜悲剧都源于那场持续了好几年的大旱灾。
说是大旱灾,其实对荒原来说,多大的旱灾都一样。不过自从种了祖父的四不像粮食之后,荒原人逐渐依赖这份额外的食物。谁想一直饿肚子呢?
所以,当习以为常的大旱灾来临时,所有人像是第一次经历般手足无措。
口粮要节约。水要节约。那时,凯蒂姑妈刚刚生下第二个孩子,可爱的男孩,没几个月就学会冲人甜甜地笑。大家给他取名叫雅各布。但也许终于对姑妈的臭脾气忍无可忍,姑父学会了回嘴,有一次吵了整整两天两夜。第三天,姑妈赌气一个人给表弟洗澡。她的动作很是生疏,废了好大力气才把孩子安置在一个近一米深的木桶里,倒了堪堪三分之一深的水——又节约又安全。但正当她拿起香皂时,外面又传来令人烦躁的噪音。她立即摔下香皂,走出去又和姑父吵了起来。等姑妈再回到浴室时,她愣住了:
涓涓水流从木桶里溢了出来,斑斓的泡沫在空中自由飘飞,把小小的房间装饰成梦幻的城堡。而在梦境的正中央,满溢泡沫的木桶静静地蹲着,寂静无声。
我那不足一岁的表弟一定很兴奋——他肯定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美丽的泡沫。于是他挥呀,搅呀。当他从深深的泡沫中被抱出来时,那张因窒息而变得紫青的小脸上,一双眼睛还大大地睁着。
我们一起把表弟埋葬。墓碑上刻着一串泡泡,下面刻着:
“雅各布·卡塔斯多夫,A.D.2167-2167”。
姑父决绝地离开了,还带走了表姐,彻底从女巫堡中消失。姑妈整日以泪洗面。她竟然开始恐惧水,见到这种透明的液体就会歇斯底里,大吼大叫,好像面对着什么妖魔鬼怪。当她犯病时,伊迪只有强行喂她几粒粉药片,情况才稍稍好转。而即使是在她最正常的时候,也几乎无法沟通,只是嘟囔着“走了……又走了……。”
“为什么要丢下我!爸爸……雅各布……我明明乖乖地呆在这里,为什么还是要离开我——”
“我知道了——水,一定是水——”
为了分担家里的事务,妈妈带着我们姐弟三个搬了回去。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洞屋时,就发现在尽头有一间小小的、还未挖完的小房间。
大旱还在继续。
让这场大旱雪上加霜的,反而是一场雨。
那是个漫长的夜晚。雨点放肆地轰炸着整个荒原。这不过是一次小雨,一场旱季的小奇迹,却也足以让荒原上的人们叫苦连天:洞屋可经不起雨水的渗透。我们全家都发动起来,伊迪在洞口和妈妈一起挖渠引水;我和路易哥哥上上下下舀积水,而卡特琳娜姐姐跑去确认其他家人的情况。
不安的气息随着雨水落入沙地,四周的闷响在我们之中弥散。但谁也说不出这份不安的来源。姑妈在房间里睡觉,她自然是不能够出门的。姑父和表姐安好的消息传来,我们稍稍安了心,继续埋头苦干。
然而,当我们回到女巫堡的时,看到的是四散翻倒的桌椅,遍布墙壁的抓痕。姑妈伏在地,好像是要冲出去寻找她的家人;她的脸却偏向窗外,惊恐地瞪着这幽深的雨夜。她头撞在了桌角上,身体早已发凉,漫天飘洒的恶魔撕扯出她的灵魂,将她投入她最恐惧的世界——
一个足以使人溺亡的,孤独的世界。
我们真是不愿意提起姑妈的死——被雨水吓死,多大的笑柄!卡塔斯多夫家的厄运又多了一个论据,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姑妈的墓碑上刻下两大两小四个手拉手微笑的小人,然后把它立在祖父的旁边。
父辈们的故事,就在此结束了。
⑤离去
荒原对我们的压迫从未平息。
十分抱歉,关于我兄弟姐妹的故事,我实在无力再叙:表姐伊莎贝尔死于沙鼠和某个荒原男人的袭击;姐姐卡特琳娜目睹了这场惨剧,强烈的刺激使她至此疯疯癫癫,在上个周六跑出了地洞,被装着物资的铁皮箱活活压成肉泥。这其中,卡塔斯多夫家被改造的基因发挥了多少作用,我不清楚。我和哥哥用铲子带回了她剩下的部分,几天没能吃下饭。而我们的父亲,早已不知道逃往何方,只留下一个空碑。
我们两个都明白,荒原容不下我们。即便我们都知道,做出这个决定的我们也许已经疯了。
不过,卡塔斯多夫家的人不就是生来的疯子吗?
于是,我们决定离开。
那天晚上,哥哥和妈妈大吵了一架。这个生于荒原的女人开始埋怨伊迪为什么要告诉孩子们那些耸人听闻的故事,为什么要让卡塔斯多夫家就此在荒原分崩离析。伊迪什么也没说,只是目光在我和哥哥的脸上来回打转。
“这就是卡塔斯多夫。”伊迪最后缓缓地说,“他们的选择,就是卡塔斯多夫的命运。”
妈妈的哭声从身后传来,路易哥哥拉着我走出了女巫堡。背上鼓鼓的背包,我回头看去,伊迪孤零零地杵在老旧的矮堡门口,在空旷荒漠中为卡塔斯多夫竖起一座巨大的墓碑。她没有挥手,仅仅是那样凝视着我们,就仿佛每一个晴朗的清晨她凝视着老屋一样,徒留下斑驳模糊的影子。我们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直到黑暗之中再无熟悉的身影。可我还是久久不愿回头,就像我知道在黑夜的另一端,伊迪也在注视着我一样。
我们来到了老屋。进入了飞船琉璃地并不是想象中那么滑,而老屋也远不如远看那样威武气派。我跟着哥哥走进去,绕了无数个弯。我发现其中一个房间里堆满了杂物,里面有好几箱白色的无字药瓶,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公民……义务……基因改造……士兵”之类的话。我捡起一个,里面装满了粉色的药丸。
我转头,看见哥哥熟练地启动了飞船,然后转动剑桥中央的投影,发现就在这片荒漠的另一面,有一座城市。
毫不犹豫地,我们把坐标设定在那里。
哥哥专心于控制面板上浮动的方块。我坐在角落里,一堆废弃的钢管之中。背包放下之后,我发现自己呼吸有些急促,却无事可做。不知怎么的,我慢慢回想起那些往事,那些卡塔斯多夫家的荒原受难史。
很快,一座大城市出现在我面前。
主脑显示这艘飞船已经被多架防空武器锁定,我已经进入危险区域。但我们视而不见,奇异的兴奋涌进我的大脑。这是城市!我马上就可以离开了——
“我是帝国贵族的人!”哥哥对着喇叭大喊,“我从荒原收容区来!我是卡塔斯多夫的人!”
一片寂静之后,更多的武器对准了我。
“未知帝国飞行器请注意,你已经进入联盟通行域。请立刻离开这片星域,否则根据联盟和帝国的临时休战条约,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
……什么?
……它在说,什么?
“此外,荒原收容区由于包庇‘帝国’分子,犯叛国罪;包庇敌方高层后裔,罪加一等,予以清洗——”
“帝国飞行器,你还有十秒,九秒,八秒……”
我跪倒在地。
现在我才后知后觉地明白了伊迪的绝望。我才想起来,为什么从来没有家人说自己是帝国的人——
荒原,是“联盟”的领地。
而卡塔斯多夫,是“帝国”的残党。
“轰!”
右边传来巨大的冲击。我在船舱中翻滚,浓浓黑烟之中,我看到几枚细长的东西,尾部燃着火焰,向荒原的方向飞去,在黑暗之中如此耀眼。
又一枚导弹击中我。我被弹飞,翻转,随着小小的飞船向下坠落。
荒诞。无助。绝望。
我想起在我坠落后不久,那片荒原也将不复存在。
理智回归身体的一瞬,我开始大笑。
我叫莫里安·卡塔斯多夫。是卡塔斯多夫家的儿子。
荒原给我们带来的伤痛、厄运,即将被返还。
但是,我丝毫不为之开心。无数的“我们”,还在人心的荒漠上跋涉。
如果那位多比·卡塔斯多夫还在,那么他一定会摘下那顶十分相称的旧礼帽,站在一大家子人之前,替我们鞠上一躬:
“女士们先生们,表演到此结束了!”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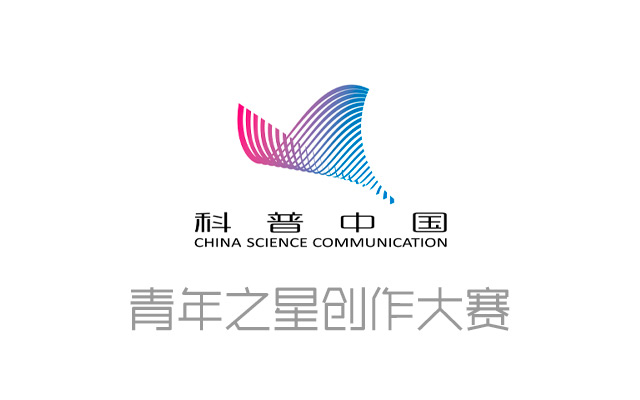
发表评论
遵守互联网相关法规,理性发言!